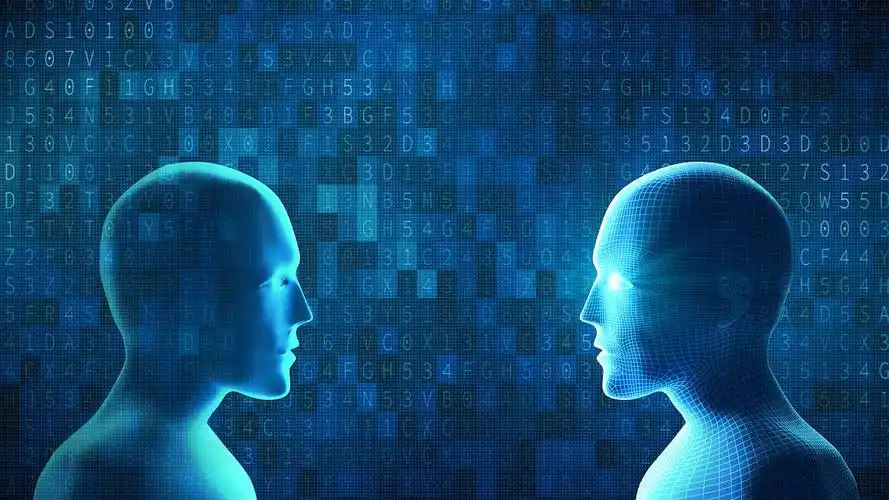一
我是個琴棋書畫樣樣不行的公主,但這並不妨礙我受寵。
因為我將我畢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如何當一名受寵的公主」這一事業中,篳路藍縷,兢兢業業。
在別的公主還在磕磕碰碰學習琴棋書畫助攻爭寵的時候,我已經熟練地學會了抱後宮各位大佬的大腿,並在諸位佳麗的修羅場裡面不改色、花言巧語、左右橫跳,堪稱後宮版端水大師。
就連我那皇帝老爹都把我抱在膝上感慨,「若是朕能像昭昭一樣,這後宮又要平和不少。」
並笑駡我鬼靈精,慣會討別人歡心。
我自然是抬起頭,晃著我的小短腿,一臉天真地說:「昭昭最喜歡父皇了。」
在這種食物鏈頂層面前,自然要擺正態度。
「昭昭上次還說最喜歡母后呢,怎麼這麼快就變了?」皇后適時地嗔道。
頓時滿座皆笑,在看到我一臉為難左右亂看之後,帝后笑意更甚。
在不斷抱大腿哄大佬開心的時光中,十年過去了,我即將及笄。
按照我前十幾年的努力,我將坐擁京城最好地段的宅院作為公主府,並依靠這些年的諸多賞賜,成為一名成功的富婆,可以養他個十個八個面首的(bushi)。
好嗨哦,感覺人生到達了巔峰……
但彼時,摸著小荷包暢想立府後驕奢淫逸美妙生活的我沒有想到,老天爺抽走了我的宮鬥劇本之後沒有給我一個 happy ending,反而蠻不講理地塞了一份權謀劇本。
並悄悄告訴我,「親,您的社畜生活還要繼續哦。」
二
大家好,我是一名成功的受寵公主,可是成功過了頭。
此時,我正坐在朝堂上,懷裡抱著小皇帝,隔著厚厚的珠簾,聽底下的大臣唇槍舌劍。
說真的,我想哭。
這不是我應該承受的。
我前世有一位著名的羅姓法師曾經說過,「人生哪怕拿到了一副爛牌,你也不能棄ẗů⁸牌。」
我曾深以為然。
作為一個前世 996 猝死的社畜,能夠以穿越的方式重活一世,我已經很感激了,況且身為一個公主日子總比平民好得多。
雖然我母妃早亡,我在後宮孤苦無依像顆小白菜。
但是沒關係,我夠努力,將公主這一身份當作事業。
握著我母妃留下的那點微薄人脈,我盡力在各位大佬面前露臉,後來成功憑藉皇后喪失幼子的東風,被抱養在皇后膝下,占了個嫡出的名頭。
後宮如職場,帝后是老闆也是甲方。
我沒想到在這個異世界,我成功做到了「將工作當作生活,將老闆的快樂當作自己的快樂」這一狗屁韭菜宗旨,苦心經營「父皇母后吹」的小可愛人設,一努力就是十幾年。
他媽的我容易嗎?
眼瞅著守得雲開見月明,我馬上就能出宮逍遙快活Ṫŭ¹,皇帝病倒了。
真人版 x 子奪嫡在我眼前展開,前朝後宮一片腥風血雨。
我和母后避居鳳泉宮。
母后生養的子女都在幼年夭折了,如今膝下只有我一人,自覺誰上位都事不關己,只淡淡拍著我的手說,昭昭別怕。
我能不怕嗎?
新的兄弟上位,我哪能有那麼好的福利?
我欲哭無淚,只能安慰自己這麼多年端水,至少誰也不曾得罪,不至於一瞬間跌落枝頭。
可惜我那些好哥哥們一個都沒贏,死的死殘的殘,誰都沒本事坐上那個位置。
還有誰?
整個朝堂後宮都在想。
此時,我顫顫巍巍地拉著一個孩子的手,走向了皇帝住的太極宮。
還有他,一個我一念之善拉到鳳泉宮避難的小皇子。
三
病榻上的父皇看著稚齡的幼子歎了口氣,最後沉沉地看著我說:「昭昭,以後……」
他卡了一下殼。
我適時地提醒到:「阿瑾,懷瑜握瑾的瑾。」
顯然兒女眾多的皇帝想不起來這個一夜風流留下的孩子的名字。
也是,誰能想到一個宮女所出,在宮裡像個雜草一樣長大的孩子,會有今日這麼大的造化呢。
「以後阿瑾就拜託你了。」父皇看都沒看旁邊的母后一眼。
顯然,他信不過姓姚的皇后,母后冷笑了一聲,沒有說話。
我一驚,「父皇!」
自古托孤沒好事啊,君不見多智如諸葛丞相,都死而後已了,我不過一個公主,哪裡承受得住社稷的重量。
「朕的昭昭啊,從小就是最機靈的,咳咳,朕有時候想,昭昭要是男兒身就好了。」父皇說。
原來他都知道啊,那些撒嬌弄癡背後的小心機,那些偶然後面的必然。
看著父皇在病中仍犀利威嚴的目光,我明白此事已成定局。
我垂下頭,拉著驚惶的趙瑾跪下磕頭,「兒臣遵旨。」
天啟二十年,皇帝崩,傳位給幼子趙瑾,又封端陽公主監國,以帝姬身份垂簾聽政。
一時,朝野譁然。
四
趙瑾今年六歲,由於野蠻生長營養不良,看起來像個大頭娃娃,遇到事只會哭唧唧地,轉頭望著我喊皇姐。
「皇姐,我看不懂。」他又在哭。
我也想哭,想和他抱頭痛哭。
雖說如今新帝剛上位,權柄都還在一干老臣手裡,大事輪不到我倆去決定,但一些雜七雜八的事,還是堆滿了案幾。
有些是確有其事,有的不過是刻意刁難欺壓幼主,我看得清楚,但實在有心無力。
俞又清就是這時候來的。
他看見小皇帝趴在我懷裡沉睡,而我坐在禦案前批閱奏章的時候,皺起了好看的眉毛。
「殿下,這于禮不合。」他隱諱地提醒我這是越俎代庖。
他到底算是君子,朝野上那群老頭,就差直接把牝雞司晨四個字寫在臉上了。
可我等的就是這句話。
於是我冷笑了一聲,甩下朱筆就準備離開。
不是我說,皇帝這活真不是人幹的,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雞早,還有巨長時間的早朝和批不完的奏章。
我想想父皇當年還有空去各個宮轉悠都滿心欽佩。
什麼是時間管理大師啊(後仰)。
扯遠了,現在我其實只想回宮補個覺。
俞又清沒想到我有這麼大反應,伸手攔也不是,不攔也不是,神色有些尷尬。
哪想到小皇帝被我的動作驚醒,揉了揉眼睛,看我欲走,也牽著我袖子,「皇姐,阿瑾跟你一起走。」
這下俞又清徹底不知所措了,無奈地彎腰朝我請罪。
我樂不可支,心想俞又清你也有今天,指了指奏摺笑道:「那這些就麻煩俞大人了。」
俞又清被我笑得紅了耳朵,半晌才喊了一聲公主,道:「下官不敢。」
五
俞又清是來給小皇帝講學的。
俞家世代名儒,俞又清的祖父正是當朝太傅,桃李滿天下。
最重要的是,俞家是孤臣,從不結黨營私,只忠於君王。
從某些層面來說,俞家或許才是父皇留給趙瑾最後的保障。
大概是入了仕,俞又清和我當年在禦書房看到的不大一樣了。
曾經的他是高山冷冽的皚雪,一身素衣仿若謫仙,出塵不似凡間客。
如今卻沉穩了很多,一身銳氣皆內化,整個人像是深不可測的湖。
我示意小皇帝跟他走。
趙瑾卻死死拽著我不肯放手,這個孩子還沒能適應身份的轉變,無助地喊了聲皇姐,像抓著一根救命稻草。
我只好歎了口氣,拉著他一起往偏殿去,「俞大人見笑了。」
俞又清自然不敢說什麼。
他開始講學,老實說,他聲音很好聽,清淩淩的。
我……聽著聽著睡著了。
我真的不是不尊重他,我這些時日又要處理父皇喪事,又要應對朝臣,還要哄小孩,實在是疲憊不堪。
至於母后,那夜之後,她就再也沒有見過我。
我是被嗚咽聲吵醒的。
一睜眼,趙瑾抽噎著望著俞又清,俞又清顯然沒遇到過這種情況,君臣二人相對無言。
我忙哄道:「阿瑾怎麼啦?」
趙瑾見我醒了,委屈巴巴地靠在我懷裡,「皇姐,嗚嗚,我,我不學了。」
懂了,小皇帝這流下的是學渣的淚水啊。
俞又清又皺眉了。
我搶在他指責之前求情道:「俞大人,阿瑾他之前沒有去過禦書房,您多擔待一些。」
我又瞄了一眼他手上的書冊,倒抽一口冷氣,《長短經》,好傢伙,夠狠啊。我還以為今天只是識識字。
我婉言道:「俞大人,今天我們還是先識字吧。」並暗示他阿瑾才六歲。
俞又清顯然有點震驚,道:「陛下這個年齡該學這些了。」
言下之意是,其他皇子從前便是這樣的。
小皇帝他更傷心了,哭得好大聲。
俞又清臉上的表情很精彩。
我仔細想起來,我今天看見他露出的表情,比以往加起來都多。
又一想,他俞大人此生走到哪裡不是人人讚揚,恐怕只在小皇帝這裡吃了這麼多癟,不覺好笑。
小皇帝還在哭,他壓力太大了,平時只是眼淚汪汪,現在哭出聲就停不下來。
俞又清徹底無奈了,將求救的目光投向我。
我含笑點了點頭,無聲說:「一個人情。」
六
趙瑾被我哄了好一會兒才消停,躲在我袖子後面覷俞又清,頗有些小心翼翼。
俞又清沒說什麼,換下手裡的經書,「無妨,陛下,我們從頭開始吧。」
他果真從最簡單的識字開始講,偶爾在趙瑾感到乏味的時候,還穿插講一些有趣的小典故。
小皇帝這次聽得很開心,眉眼飛揚。
我看了一會兒,便去拿了奏摺在旁邊繼續批閱,批累了就抬頭看看俞美男子洗洗眼,自然是美名曰其查看授課進度。
不記得宮人撥了幾次燈燭,今日的授課才結束。
小皇帝勉強起身拜別老師,我看著他哈欠連天的樣子,便對俞又清客套道:「陛下年幼,怕是已經乏了,便由本宮代他送送大人吧。」
說是送送,我只是稍稍做了個起身的動作,顯然十分不走心。
「勞煩殿下了。」俞又清垂眸道。
……
我真的只是客氣一下。
確實已經很晚了,即使是皇宮,很多處都熄了燭火。
我命宮娥們都提燈去前方映路,一時便只剩我和俞又清二人。
「俞大人,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殿下,你希望陛下是什麼樣的?」俞又清轉頭問我。
長風吹過宮道,我一瞬間就清醒了。
自我聽政以來,有人暗自唆使,有人存意試探,問來問去也不過是一個意思——趙昭,你想不想掌控朝政。
我盯著俞又清笑道:「若是我想把小皇帝養成傀儡呢?」
俞又清仿佛沒聽出我的嘲諷,他幾乎是篤定地說:「這不會是殿下所願。」
「哦?」
「殿下連魚食都懶得細細拋。」
?
我一下噎住,剛為了符合此情此景裝出的高冷神情一下破功,懊惱道:「俞又清!你有完沒完,不就是不小心灑了你一身嗎?你怎麼抓著不放呢?」
昏暗的宮道,攝政的公主和忠臣,怎麼看都很適合大家說些似是而非的話,互相鬥鬥權謀,你偏說什麼魚食。
黑夜中我好像聽見他笑了一聲,轉頭去看,他卻又是一副冰塊臉,只是聲音柔和了很多,「殿下,我不是怕你心存欲望,是怕你無所欲便不在乎。
「就比如,你要是無所欲,陛下再看不懂奏摺,你也不能一人獨斷。
「你是自覺無心皇權,皇帝尚幼,你理所當然地代勞,但別人會怎麼想,陛下若是長大了又會怎麼想。
「有些事情,總是得從開頭便在意的。」
我一瞬間了悟。果然,論起避嫌,他們俞家才是大師,不然也不會在奪嫡中還能獨善其身。
我望著宮門含笑道:「長路漫漫,還請俞大人多多指點。」
俞又清看著我好像還想說些什麼,最終只是淡聲說了聲好。
不知是不是錯覺,我總覺得他目光灼灼,灼得我面熱。
不知覺已快行至宮門,俞又清轉身向我告別。
天邊的晨光絲絲縷縷,將欲突破夜色。
七
趙瑾其實很聰明,從他能在毫無依仗的狀況下保命至今,又能在奪嫡時逃入我宮中尋求庇佑就可見一斑。
他很快堅強起來,不再是只會牽著我的袖子躲在我身後的小哭包。
我受俞又清點撥後,不再獨自批閱奏摺,倒也樂得自在,每天支著下巴,聽俞又清給小皇帝講課。
雖然俞先生講得很好,但這些知識對我而言到底過於簡單,總是聽著聽著就走神,眼神飄向講課的人。
俞又清看了我好幾眼,終於某日下課後,無奈問道:「殿下,下官是有何不妥嗎?」
我老神在在,一本正經,「並無,不過是眼見丁香笑,鼻嗅蘭麝噴,難免燈下看美人罷了。」
俞又清啞然,一張玉面染上紅意,半晌才瞪了我一眼,「胡說八道!」
小皇帝在後面哧哧笑了幾聲,笑得俞大人面色愈紅,今日奏摺都不看了,拂袖而去。
「唉!」我怕真的把人惹惱了,忙忍著笑起身去追。
俞大人在前面走得急,身上配的玉晃蕩得叮噹作響。君子佩環玉,意在提醒自己注意儀態,行道不可急,他似是聽見玉聲,又緩下步。
我急走幾步便趕上了他,「俞大人,夜色深厚,你可慢些走。」
這些時日,我們像是有了默契,每日結束後,都由我送他出宮。
俞又清一開始總慢我一步,不遠不近地墜在後面,有話要說才上前來,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兩人都習慣了並肩。
俞又清這次像是真的生氣了,我說什麼,他都回應得很冷淡,弄得我心裡惴惴的。
眼看著就要到宮門口了,我咬了咬牙,拽住他的衣袖,「俞又清,不好意思啊,我以後……」
「殿下,」他直直打斷我,望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只歎了口氣,半晌才開口,語氣很是挫敗,「你別總是惹我。」
我從沒見過俞又清這般神態,他總是冷淡又驕傲的,現在卻認輸了一樣地看著我,眉眼微垂,看上去甚至有些委屈。
他笑了笑,有些自嘲,「殿下,你總是喜歡逗我,可是這不好玩。」
我愣住了,手裡宮燈的燭火劈啪作響。
八
我和俞又清相識在一個春季,彼時我犯了春困,懶懶地靠在亭榭上,往底下的湖裡拋魚食。
哪想到剛巧,俞又清從亭榭下長廊裡過,不知哪裡來的一陣風,不偏不倚將灑落的魚食吹了他一身。
他一抬頭,我拋魚食的手還沒收回來,被他抓了個正著,只好尷尬地笑了笑。
二哥哥一向與俞又清不對付,大聲笑道:「俞公子走哪裡不是被香囊盈果投身,現下卻當了回魚。」
俞又清當時也不過是十五六歲,卻已經十分沉穩。他對二哥哥的譏笑置若罔聞,只是靜靜地撣落了魚食,對我們行禮之後,就隨宮人離開了。
被二哥哥這麼一打岔,我甚至沒來得及正兒八經道個歉,心裡頗有些歉疚。
傍晚,父皇召我去用膳。
父皇是皇子的時候,分封在邊疆,不習慣講那麼多規矩,偶爾會為了以示親近,留一些大臣吃晚膳,說一些家長里短。
到底君臣有別,怕他們不自在,他便常常召我去陪吃,主要是由我去熱場加捧哏,附帶演演父慈女孝。
這也是我作為公主的一項重要業務,為了辦好它,每次去之前,我都要想好幾個合適的段子,使他們君臣盡歡,往往一頓飯吃下來,我臉都笑麻了。
我一到,父皇就笑著讓我坐他身邊,朝下首的老者道:「太傅,這是昭昭。」
他又看了我一眼,故意調笑,「招人喜歡的招。」
我尷尬到腳趾撓地撓出大明宮整宮。
我被收養到皇后膝下後,陛下讓皇后給我改個名字,說是原先的太小家子氣配不上嫡公主的身份。
帝后二人挑選後用了昭字,取昭如日月之意。
彼時我仗著年紀小撒嬌弄癡,「招招好,招招要招人喜歡。」還做作地原地轉圈圈。
靈魂老阿姨仗著蘿莉身撒嬌已經很羞恥了,現在被扒黑歷史更是恥上加恥。
我甜笑地嗔了一句「父皇!」,並且已經預想到這成為一個梗在此後同類場所中不斷上演的未來,心梗得無以復加。
父皇果然笑得更開心了,一時在場者其樂融融,父皇指著席下一少年道:「昭昭,你瞧瞧人家又清,你還昭招不分的時候,人家就出口成章了。」
那少年應聲抬頭,我一怔,發現這位被讚譽的「又清」,就是今天那個倒楣催的俞公子。
見我面色有異,懂眼色的宮人早就繪聲繪色地在父皇耳邊並不小聲地講起了今日魚食事件。
古代人笑點這麼低的嗎,又是滿座皆笑。我麻了。
好傢伙,今天的段子白準備了。
俞又清靜坐在那裡不發一詞,畢竟我是公主,縱使是他占理,也不好說些什麼。
我自覺對不起他,走上前朝他道歉,免得他不尷不尬的。
他暗暗舒了口氣,朝我感激地遞了一瞥。
弄得我更不好意思了。
散席之後,我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對他不住,想起某次生辰收的賀禮之中有某個古籍孤本,便悄悄拿去禦書房遞給他,權當賠禮。
俞又清沒有收,只道不過一件小事,眼神卻沒忍住,往書上又瞄了一眼。
我看出他心喜,強行往他手裡一塞,「俞公子,這書於我不過一堆廢紙罷了。」
我看了看他的臉色,「你若過意不去,就當交換,明日此時,我要吃到宮外陳記糕點。」
俞又清這才紅著臉收了。
第二天,他果然信守承諾帶來了糕點,滿滿一大食盒。我被這分量驚到;了。
俞又清有些不好意思,「忘記問公主喜歡什麼,就每一種買了一些,望公主不要嫌棄。」
這孩子也太實誠了。
或許是那天晨光太耀眼,少年的眸光映到了我心上。
我開始隔三岔五地往禦書房跑,帶著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送給各位哥哥,也,送給俞又清。
我送給俞又清的,是精挑細選之後覺得他會喜歡的,但有時候,也會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俞又清顯然奉行「來而不往非禮也」,不論收到什麼,第二天總會從宮外給我帶一些東西回禮。
我一度有些挫敗,覺得這個人不愧是高冷之花,客客套套的,難以接近。
於是某一次收到東西後,只冷淡地道了謝,第二天沒有再來。
可是俞又清托三哥哥給我遞來了一份酸梅膏,又留了一封信,問我是不是他昨天送的不合心意,說下次不會了,在信的末尾,像是猶猶豫豫地加上了一句,陳記又出了新品。
我很難形容當時的心情,只是默默在榻上扭成了蛆。
我又可以了。
翌日我又去了禦書房,俞又清遞上一個小盒子,我拆開一看,笑道:「這不是月前出的嗎?」
俞又清紅了耳朵,低聲說:「嗯,是我記錯了。」
柳絮隨著東風飛過,不知道是誰的心揭開了春帷,一點點絮飛也蕩起漣漪,激起迴響。
九
少年人的情意風吹就長。
剛穿越的時候,我從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愛上一個古人,現在卻每天在想,我一定要搞到這個男人。
我去禦書房越發勤快。
我甚至毫不矜持地想,俞又清臉皮薄,我先表白也沒有關係。
可是心草還沒漫天遍野,野火就先來了。
有一天,父皇站在我身前說:「昭昭,換個人吧,俞又清不行。」
我當時茫然地睜大了眼睛,才恍惚想起來,本朝只有尚公主、招駙馬一說,如果同我在一起,俞又清就不能再入仕了。
顯然,俞又清是父皇看好的下一代股肱之臣,容不得我染指。
更何況,我清楚俞又清清冷外表下的赤誠,他或許心有風月,但更有山河。
我低頭眨掉眼裡的淚意,朝父皇笑著說:「好。」
父皇摸了摸我的頭,「朕的昭昭可以要更好的,昭昭要什麼都可以。」
「這可是您親口說的。等我出宮立府,我就養他個十個八個面首。」我努力讓語氣雀躍一點,眼淚還是掉了下來。
我是一個受寵的公主。
要想受寵,得聽話。
我再也沒去過禦書房。
俞又清托幾位哥哥給我捎了信,我沒有看,只是連著他送給我的東西一併還了回去。
再後來就是父皇病重,局勢紛亂,曾經在禦書房共讀的那些人早已反目成仇,刀劍相向。
那一年的春日,到底是回不去了。
等到再見面,我是攝政公主,隔著珠簾坐在朝堂之上,他是臣子,低眉斂目跪在朝堂之下。
如果不出意外,他會一路扶持趙瑾成為一位合格的帝王,而我功成身退,從此漸行漸遠。
他說得對,我不該因著放不下就繼續撩撥他。這樣對誰都不好。
可是此時,說著「不好玩」的俞又清站在我身前,卻並沒有轉身離開。
明明宮門只有一步之遙了。
他抬頭望向我,像是在等一個答案,又或者,像是在等一個審判。
我有些不明白,對他而言,明明是同我再開始才更虧,但血液卻開始瘋狂地躁動起來。
我甚至聽見夜風拍在我面頰的聲音,在耳膜邊一陣一陣地鼓動喧囂,心尖也仿佛沾上了那年的柳絮,惹得人癢癢。
我抬手將宮燈遞給了他,「俞大人。」
他眼裡的星光黯淡了下去,不鹹不淡地應了一聲,卻不願意拿那盞燈,渾身上下寫著拒絕。
我忍了忍笑,「都說了長路漫漫,大人不願意繼續與我並肩了嗎?」
那片星河又開始璀璨了。
我第一次真正看見了俞又清克制不住的笑意,他笑著說:
「榮幸之至。」
十
我同俞又清秘密的地在一起了。
現在這個時候,俞又清同我都不能拋下身上的擔子,不負責任地在一起。
我們依然只有授課和走到宮門那一段路的時間。
俞又清雖然還是冷冷淡淡的,但是個人都感受得到他的春風得意。
朝堂上的老臣只當他討了新皇的歡心,更加不喜,參他的奏摺都多了幾本。
我故意當著他的面念,趙瑾已經徹底被這個老師折服了,狠狠用朱筆披了駁回——他現在的字已經寫得像模像樣了。
夜間回去,照例宮娥們遙遙在前,我提著燈同他在後。
「這麼開心嗎?」我笑他。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俞某修身ťū́ₖ不過爾爾,卻能有幸先齊家,怎麼不愉悅?」他咬重了齊家兩個字,反問我。
好哇小俞你變了。
我被撩得面紅心跳,卻也不甘示弱,悄悄瞥了宮娥們一眼。
「俞大人最近被那些老狐狸罵得好慘哇。」我踮起腳尖。「本宮自然得安撫一下,俞大人,你說是不是?」
後半句含含糊糊在了唇齒之間。
俞又清愣在了原地,好一會兒才伸手撫了撫唇。
「甜嗎?我剛吃了糖。」我在他耳邊用氣聲問他,他的耳朵和臉登時紅了大片。
「胡鬧。」他輕斥,眼裡卻染上笑意。
廣袖下的手,悄悄地拉在了一起。
十一
我們還沒甜蜜幾日,科考開始了,俞又清被任命為主考官ťũ₁,每天忙得腳不沾地,有幾日連趙瑾的授課都中止了。
我在朝廷上應付那些老狐狸,也是心力交瘁。
總算忙完了會試,殿試後我們三人一起擬前三甲。
這是趙瑾登基之後第一次科舉,各方勢力都鉚足了勁,往裡面塞自己的人,可惜監考的是俞又清,鐵面無私,最後脫穎而出的皆是有真才實學之輩。
前三位更是水準相仿,勉強定下了狀元,剩下兩位連俞又清都犯了難。
我和趙瑾自然沒有俞又清的學識水準,乾脆當甩手掌櫃由著他糾結。
但時間不等人,眼看著日頭都要西斜了,俞大人還是沉吟著不說話,我建議道:「不如那位張生就當探花吧?」
「為何?」俞又清問。
「自古俊秀者為探花,我看那位張生儀錶堂堂,不妨就他了。反正榜眼探花也差不離。」
「公主所言甚是。」俞又清面色沉了沉。「俊秀者可為探花,下官倒是覺得李生相貌更佳。張生便當榜眼吧。陛下,您覺得呢?」
趙瑾看了我倆一眼,一錘定音,「還是張生為探花吧。」
看來還是我倆審美一致,我讚賞地看了他一眼。
俞大人自閉了。
出宮的路上,俞大人悶著頭不說話。
「怎麼了俞大人?」
俞又清斜睇了我一眼,抿唇不語。
「好吧,那我也覺得張生不若李生顏色好,你看如何?」
俞大人的唇抿得更緊了。
「不過本宮倒是覺得,在場有一人遠盛這二位,他那才是風姿驚人,使人心折不已。」
「誰?!」俞又清忍無可忍抬頭望我。
然後撞進了我含笑的眼裡。
俞大人臉又紅了。
他瞥了眼宮女,突然一把把我拉入了一個拐角,彎下腰和我額頭相抵。
他第一次喊我昭昭。
他說:「昭昭,你別看著別人。他們都不會有我好。」
然後小心翼翼地將一個吻印在我嘴角,頗有些小氣地說:
「你是我的。」
十二
清靜的日子沒過多久,姚家派人來見我,托母后的關係,我還客客氣氣地喊了聲姨母。
世家果然沉得住氣,姚夫人一副來看侄女的樣子,連小皇帝都沒見,不過一盞茶的工夫就告退了。
保險起見,我還是和俞又清商量我們二人得更隱秘一些。
如今朝野之上,小皇帝只有俞家帶著保皇黨勉強抗衡世家。
俞又清不能在這個時候當了我的駙馬,尤其是被迫。
於是,俞大人每天晚上的親親抱抱都沒有了。
俞大人很不高興,帶著手下一幫人,充分發揮文臣的優良傳統,先是朝野之中冷嘲熱諷,再在奏章裡彈劾背刺,下朝後還暗戳戳寫文章,譏諷世家權臣蛇鼠一窩。
關鍵他們文筆是真的好,辭賦詩歌、話本歌謠、樣樣開花,筆名還換得賊快,逮都逮不著。
一時之間我朝現實主義文學大興,民眾文化氛圍飆升。
世家自然不堪示弱,兩班人朝上朝下鬥得不可開交。
我和小皇帝坐在上位渾水摸魚,時不時還煽風點火。
但我沒想到現世報來得這麼快。
幾日後,一俊秀青年來到端陽公主宮外的府邸,自稱公主與其有救命之恩,現來銜草結環相報,願意入府侍奉左右。
香豔軼事總是傳得飛快,等傳到宮裡的時候,才子佳人的故事已經發展到公主珠胎暗結了。
我本來好端端地吃瓜,心想,蕪湖,我哪個姐妹真的好豔福啊。
直到宮人悄悄說出公主的封號,我手裡的瓜子才掉下了地。
端陽,這不正是在下嗎?
好牛,我和人都珠胎暗結了,竟然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忙喊人備好車架,去看看這位以身報恩的青年什麼來頭。
走之前,我跟剛過來準備授課,現在卻黑著臉的俞大人指天咒地地發誓,這絕對是碰瓷,我一定會處理妥當,才稍稍把人哄好。
等我到了現場,青年抬起頭喊了一聲殿下時,我心裡就一個咯噔。
完了,俞又清要把自己酸死了。
十三
我同這位確實存在救命的恩情,不過不是我救他,而是他救我。
多年前的冬日,是他從冰湖裡救出來了一位不受寵的小公主,而後,那位命苦的小公主再睜眼換了一個靈魂。
後來我受寵之後,求母后賞他些好東西,母后只是搖了搖頭,說昭昭,他不過一個庶子,偶然有幸進宮救了你,是他的福氣,再多的他就受不起了。
我聽懂了母后的意思,怕是他在府中境遇並不好,給了什麼也護不住,於是只好悄悄托人給他遞了話,讓他日後有什麼難處盡可來尋我。
現在,姚昱跪在我身前求我將他留下,眼睛裡滿是難堪和屈辱。
不愧是姚大人,這種陳年舊事都能翻出來。
姚昱看我猶疑,狠狠叩了幾個響頭,額頭上都迸出了鮮血,「公主,我求您了,姨娘還在父親手裡,我求求您了,將我留下吧,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慌忙制止他,無奈地歎了口氣,讓管家給他收拾個院子。
我說:「姚昱,我不要你做什麼,你要是爭氣,就自己想法子討回今日的屈辱。」
然後我灰溜溜地回宮去哄俞大人。
俞大人見我那個樣子就知事態不對,等我說完前因後果,已經快把自己醃成酸蘿蔔了。
「原來還有這般緣法。」俞又清大概是想譏諷幾句,但看到我可憐兮兮的樣子,還是自己去生悶氣了。
我照例送俞又清出宮,不過今日我尚有話問姚昱,便也打算回公主府一趟。
俞又清還沒發作,趙瑾就扯著我的袖子不依了。
自他登基之後,我一直在宮內陪著他,公主府只是一個擺設,如今離開他出宮過夜確實是第一遭。
我只好彎下腰哄他。
等ŧŭ₀哄完小的,大的也是低著頭像霜打的白菜,默默地等哄。
可惜實在沒時間了,我只好借著袖子,輕輕用手指勾了勾他手心,權做安撫。
十四
等我和姚昱談完話已月近中天,我回了自己房間,卻瞥見一抹暗影。
來不及驚叫,他已經捂住我的嘴,「昭昭,是我。」
我下意識看了看四周一眼,「你怎麼來了?」
俞又清神色黯淡了些,「有一會兒了,你放心,我很小心,沒有人會知道。」語氣頗為委屈。
「又清,你再忍忍。」我知道他最近都不大痛快,又委實沒什麼好辦法,只好柔聲勸他。
「我不是怪你。」俞又清好像喝了點酒,眼神有些朦朧,含著一層薄薄的水光,「可是昭昭,我抓不住你。
「陛下可以扯著你的袖子讓你別走,可是我不可以。
「我們甚至連親近一下都要在無人的黑夜裡。
「現在連親近都不可以了。」
俞又清越說越委屈,像是一隻垂頭喪氣的大狗狗,「昭昭,我從來沒有這麼不知所措過,我怕你,就像從前一樣,說不來就再也不來了。
「我從小只學過詩書,沒人教過我怎麼和心儀的女孩子說話。我很糟糕又太笨拙,有什麼事情還țū³要你來哄我,明明都不是你的錯。
「但是我都會改的,你別不要我。
「我會比任何人都對你好的。」
月色透過窗,明明是清峻仿若謫仙人的俞又清此刻卻像是最卑微的凡世求愛兒郎,他自覺一無是處又一無所有,只能將自己的一腔真心剖出來Ţū⁻給心上人看,祈求她能夠垂青。
我突然意識到,在我們這場戀愛裡,俞又清才是那個賭徒,他孤注一擲地賭上了所有的前程,但卻沒有換來一點安全感。
「俞又清。」我一出口才發現,我的聲音裡已經帶了哭腔。
「昭昭,你別哭。」俞又清慌了神,有些自責,「我來不是讓你哭的。」
他像是終於想起了今夜來的目的,有些局促地匆匆解下了發帶,對我笑道:「公主,下官沒什麼救命之恩,今夜不為報恩。
「下官今夜來,是來自薦枕席的。
「還望公主垂青。」
對不起諸位我只是個俗人,此情此景,墨發垂腰衣衫半解的俞又清,讓我什麼感動自責都沒了,我的思想只能直奔下三路。
楚天雲地把臂同遊後,牡丹塵柄都濕透,我懶懶地伏在他身上笑道:「俞大人好生孟浪。」
「昭昭。」俞又清酒勁下來了,窘迫地紅了臉。
「沒什麼,俞又清,我喜歡你這樣。」我親了親他,「我愛你。」
他一下怔住,半晌才啞聲不住喊昭昭。
喊得我腰都斷了。
十五
趙瑾十歲那年,我和俞又清已經在一起將近四年。
我尋思著趙瑾也差不多能當起一些事了,此時,姚昱已經掌控了半個姚家,我乾脆不再藏拙,將大半底牌都掀了出來,聯合俞又清狠狠打壓了一番世家。
姚大人乞骸骨的那天,我們都很開心,俞又清問我:「殿下怎麼這麼著急?」
我氣定神閑,「因為本宮想嫁人了。」
趙瑾早就看出我們之間的曖昧,他雖年紀還小,但早就在權力中脫去稚氣,笑笑之後又皺了皺眉,「老師要當皇姐的駙馬了嗎?」
「不是,是我嫁人。」我指了指自己。「阿瑾,規矩都是人定的,你就當皇姐這回求你。」
「殿下。」俞又清斥道,又柔了聲音,「你不要委屈自己,如今大局已定,我……」
「別別別,阿瑾還需要你呢,至於我,我早就不想幹了。」我笑道。
社畜這麼多年,終於能退休,我簡直想喜極而泣。
「況且俞又清,你三媒六聘流程走快一點。」我催他,「到時候我穿嫁衣不好看了我打死你。」
「什麼?」他愣了半天,才緩過神來看我的小腹。
這一次,才子佳人,公主珠胎暗結的流言是真的。
(正文完)
俞又清番外·思卿昭昭與暮暮
一
在遇見昭昭之前,我被教導如何成為一名君子和忠臣,可是遇見她之後,我學會了成為我。
成為俞又清。
知他所願,了他所欲。
二
俞又清第一次見到這位端陽公主,被魚食劈頭蓋臉撒了一身。
她倚在欄杆旁朝他歉意地笑,聽見皇兄的譏諷,還惱火地瞪了一眼,半點沒有皇室子弟的倨傲。
彼時俞又清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並沒有放在心上。她不是故意的,此事便罷了。
沒想到陛下的晚宴再相逢。
她處在皇帝和諸多重臣之間,言笑晏晏,落落大方,還含笑幫他解圍。
俞又清微舒口氣,一抬頭卻看見少女朝他俏皮地眨了眨眼,像是在無聲地說「抱歉呀。」
他第一次見到這麼活潑主動的姑娘,不好意思地微低下頭,只心道非禮勿視。
但陛下說的那句「這是朕的昭昭,招人喜歡的招。」卻不期然在他耳邊回蕩。
俞又清喝了口酒,心道此言果然不虛。
三
俞又清說不清,自己是什麼時候對公主產生了非分之想。
或許每一次她來禦書房,這種非分之想都會多一點。
因為她望著他的樣子,是那樣的緊張和歡喜,盈盈的雙眼像夏夜滿映著星輝的湖水。
那樣燦爛,又觸手可及。
怎麼能不讓人心動?
年少的俞又清不知道怎麼去對待這份真摯的情意,只能像是第一次收到糖果的孩子一樣,既不捨得吃掉,又捨不得那點甜意,只好小心翼翼地抱著那塊糖,一個人躲起來慢慢地舔舐。
所以哪怕俞家距離陳記有半個城的距離,他也願意早起一個時辰趕過去幫她買。
他下意識地想讓那塊糖存留的時間久一點,再久一點。
俞又清承認,在趙昭面前,他從來不是君子。
趙昭曾問他是不是來而不往非君子,他才給她回禮。
俞又清心想,私收女子禮物,甚至一直稱得上互通有無,又算哪門子君子?不過是他修身修心不夠,對送禮的那個人心搖神移,情難自抑。
只是這種話怎麼說得出口?
祖父教過俞又清怎麼寫出驚世的詩文,先生教過他怎麼在宦海裡浮沉,卻沒人教過他怎麼去討好自己喜歡的姑娘。
真的遇見那個人,再含蓄的詞句好像都顯得冒犯又孟浪。
於是他只能小心再小心地遣詞造句,寫廢了一張又一張的紙,最後只問道:「你明日還來不來?」還要畫蛇添足地加上一句,「陳記好像出了新品。」
送信的那一整天,俞又清都神思不屬,他第一次對自己產生了質疑。
他想,俞又清你真是太糟糕了。
但是這麼糟糕的俞又清,願意為了趙昭去努力改變,變得更讓她喜歡一點。
真希望她願意等一等他。
四
可是趙昭沒有等。
她放棄了。
那幾天俞又清被祖父罰跪在祠堂。
祖父的戒尺一下一下抽在他身上,失望又憤怒地說:「又清,你多年詩書就只學會了兒女情長嗎?」
俞又清說不是的,我依然願意成為奉身山河的俞家兒郎,但我也想成為耽於她眉目的俞又清。
前者畢生所志,後者今世所喜。
或許難兩全,但他平生第一次這麼叛逆地想去挑戰規矩。
俞又清直到被打暈過去都沒有鬆口。
他只含含糊糊地想,不行,我還沒有告訴過公主我的心意。哪怕她只是含羞地看我一眼,我都願意不辭艱險地走下去。
可是趙昭再也沒有來過禦書房。
送給她的禮物,也被退回到俞又清手上。
俞又清被請家規的時候沒有哭,被雙親祖父指責的時候沒有哭,卻在那時候怔怔地落下了淚。
他曉得她也有不得已,或許是為了他的前程,又或許也為了自己。
但為什麼不過來,哪怕只是問一問他呢?
別這樣,好像是只有他一個人沉迷在了這場虛幻的美夢裡,自顧自地感動與深愛,最終不能自拔,演了一出獨角戲。
那個人卻連最後謝幕喝彩都不願意。
俞又清有些委屈。
五
俞又清看著他的公主拉著小皇帝走上高位。
她微揚起下巴,脊背挺得筆直,像一隻展翅的鳳凰。
所有人都說端陽公主心機深遠。奪嫡奪得腥風血雨,卻是她在幕後憑女流之身成了最後贏家。
祖父猶豫地讓他去探公主的口風,擔心她竊國。
俞又清說,不是的,祖父,她不是這樣的人。
他最瞭解他喜歡的姑娘,她心軟又憊懶,聰慧又不失原則。
先帝也正是如此,才會在所有人裡堅持選擇了她。
所以再相見,俞又清只悄悄提醒他的姑娘,人言可畏,你要謹言慎行,你要保護好自己。
六
俞又清曾經覺得這樣也不錯。
朝上朝下,他和她,既是朋友又是同袍,一起攜手幫小皇帝拔掉朝野的釘子。
不論會不會出現另一個人,他們都會是彼此最堅厚的倚靠。
可是俞又清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她。
有下屬暗示他,該不該給公主選一個駙馬,最好出自清流世家,就差把選個自己人寫在臉上。
他明白下屬的顧慮,無非是想綁得更嚴密一些。
可是他只是稍微想像了一下,有一個男人出現在公主面前,她或許會對他說甜言蜜語,甚至可能親吻他,就覺得難以忍受。
下屬看了一眼他的臉色,大概也覺得這樣不光彩,頗有些賣子求榮的意思。於是小心翼翼地改口,「那不然,我們送送男寵也行。」說不定還能父憑子貴,嘿嘿。
還男寵,一個駙馬不夠他心梗是不是?
一群試圖取悅公主的男人……
俞又清呼吸一窒,瞬間嫉妒得發狂。
過去的委屈甚至是怨懟一齊湧上心頭,
趙昭,憑什麼只有我這麼喜歡你啊?
七
一忍再忍,俞又清還是攤牌了。
趙昭說,俞大人願意和我並肩嗎?
俞又清顫著聲音道,榮幸之至。
他其實想說,不只是朝廷和宮道,往後餘生,我都只想和你並肩。
所愛隔山海沒有關係,我可以走,也可以等。
只要你願意同我一起。
八
當年無意灑下的一把餌食,
引來了願者上鉤的少年郎。
於是後來,俞又清成了趙昭的小俞(魚),趙昭成了俞又清的暮暮朝朝。
成婚番外一
趙昭成婚的那一天,整個皇城都掛滿了紅綢。
趙瑾說,皇姐,我之前年幼,事事都靠著你,如今也總算可以為你做些事了。
趙昭是本朝第一位下嫁的公主,趙瑾怕她受委屈,事事都要求個最好。
現在他一邊說,一邊還是紅了眼睛。
他早已適應了君王的身份,近一年幾乎能做到喜怒不行於色,頗有人君之風。
但是在趙昭以金扇掩面被喜婆牽著出門的時候,還是沒忍住掉了眼淚。
姚太后也來了。
她雖然難以釋懷先帝和姚家的事,但到底是一手養大的孩子,大喜的日子于情於理都得過來。
她拿著梳子幫趙昭梳了三下頭,神色淡淡,但最後還是道:「他要是對你不好,你便回宮來。」
趙昭點了點頭。
她乘上了轎,即將出宮門的時候,忍不住挑簾回望了一眼。
背後是層層宮牆,鎖住了她人生前二十年。如今是真的要告別了。
趙昭這才感受到一點緊張,攥緊了手上的金扇,但是目光觸及扇下的墜子,又笑了笑,想起來一個傻瓜是如何笨拙地一點點把墜子串好,系在她扇下。
他是那樣的歡喜,幾近哽咽地抱著她喊昭昭。
於是她沒再回頭望。
因為她知道,前方是靜好歲月,此生情長。
二
俞又清已經在宮門口等著了。
他一身紅衣,愈發襯得墨發如鴉,肌膚似玉。
趙昭悄悄打開簾子想瞅一眼。
俞大人私服都是統一的月白黛青等素色,她還沒見過他穿紅衣呢。也不曉得那般俊朗出塵的郎君,穿上紅衣是個什麼樣。
沒想到一挑開簾子,兩人就對上了眼,兩人都一怔,又匆匆別開了頭。
明明都在一起這麼久了,這一刻還是都紅了臉。
可是羞著羞著,又忍不住從心裡蕩出笑來。
一行人浩浩蕩蕩到了俞府,喜婆掀開簾,俞又清忙遞手牽她出來。
幾乎是趙昭一搭上他的手,他就緊緊反扣了回去,低聲在趙昭耳邊說小心臺階。
因為趙昭有了身子,便用了去扇禮,現下不過半遮面,哪裡看不見眼下的道路,不由好笑得看了他一眼。
趙昭身份貴重,既是嫡公主又曾攝政,因此高堂是俞又清祖父,受新人跪拜的時候還略偏身避了避。
婚禮的流程走了個遍,俞又清的手就沒有松過,直到把人送進洞房了,還不舍地坐在喜床上。
「該去敬賓客了呀。」趙昭提醒他。
「嗯。」
「一會兒陛下該來了。」趙昭實在好笑,推了推他胸膛,俞又清這才起身。
等到夜間俞又清回來的時候,已經被灌得有些醉了。
趙昭聽侍女說趙瑾灌得最凶,仗著自己是陛下一杯一杯地賜,最後還惡狠狠地說:「先生若是對阿姐不好,朕可饒你不得。」
俞又清走路都有些不穩了,趙昭去扶他,他就半抱著她不肯鬆手。
他把頭半搭在她肩上,聲音有些飄忽,「昭昭,我覺得就像做夢一樣。」
這麼多年了,昭昭終於變成了他的昭昭。
趙昭輕輕把他扶正,在他唇上咬了一口, 笑著問:「醒了嗎?」
俞又清也跟著笑了。
綢繆束薪, 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番外
婚前俞又清一度擔心趙昭和自家長輩合不來。
俞家家風嚴正, 說得難聽點頗有些古板,規矩繁多,俞又清從小就被養得端莊守禮、老氣橫秋,只在趙昭面前才會怨會笑有了人氣。
於是他悄悄給兩邊做工作。
趙昭不以為意, 調笑他, 「俞大人, 本宮別的不擅長,討人喜歡可是專業的。」
他又回去對家裡說, 趙昭身份貴重, 難免有的地方驕縱一些, 況且如今有孕,無論如何都請不要將俞府的規矩放在她身上, 實在不行……。
他祖父一下子把茶盞扣在桌上, 「你說什麼?」
俞又清絲毫不怕, 「實在不行,孫兒就和昭昭暫時搬去公主府。」
「我說前一句!」老太傅早就知道自己孫兒一顆心落在公主身上, 這麼多年守身如玉的,他們也看在眼裡,還操心過俞家幾代單傳,怕不是得斷在俞又清這一代。
現在公主願意屈身下嫁,兩人得成連理,俞家長輩都暗自松了口氣。
老太傅也曾感歎公主情深, 願意照顧又清前程。
同時內心深處也頗為自得,畢竟這麼優秀的孫兒是他一手教養出來的。
如今卻曉得,自家孫子原來在婚前就讓人家公主有了身子。
難怪成婚急匆匆的。
老太傅氣得眼前發黑。
那廂俞又清還在怕他們覺得趙昭不矜持, 一口咬死是他先引誘公主。雖然事實也的確如此。
老太傅聽不下去了, 一杖敲在他背上, 老淚縱橫,「臣愧對先皇!」
俞又清一蒙, 稀裡糊塗地就迎來了一頓家法。
最後還是趙昭給求情,這事才算過了。
俞又清趴在榻上,疼得眉頭直皺。
趙昭一邊給他擦藥, 不由心疼,「俞大人這麼聰明的人,怎麼這時候轉不過彎來, 偏在那裡討打。」
俞又清就轉頭看她,滿目柔和,「但這樣祖父就能更喜歡你了。」覺得對你不住。
趙昭啞然。
「下官如此殫精竭慮, 公主應當獎賞下官。」俞又清晃了晃她手指。
然後他得到了一個吻。
小劇場
趙昭顯懷之後,孕期反應突然變得很嚴重,幾乎吃不下什麼東西, 吃什麼吐什麼。
俞又清急壞了, 宮裡的禦廚都請來了,天天哄著她吃。
據不知名女婢透露,俞大人曾經像大狗狗一樣垂頭喪氣地向公主道歉, 說昭昭,我沒想過會這樣的,你別生氣。
弄得公主又好氣又好笑。
□ 寒棲